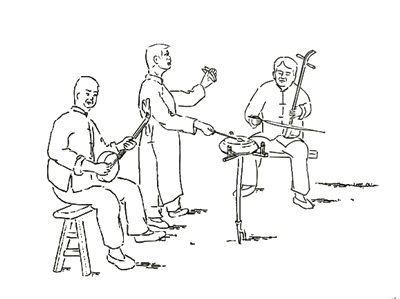编撰《河洛大鼓志》的《人物志》,要整理新安县河洛大鼓名艺人王管子的个人简介,需要配上照片,但手边没有,网上也找不到,就一再委托原阳曲艺届的朋友薜涛帮忙采访一下王管子,顺便拍一些照片。今天终于看到了薜涛老弟发过来的照片。太高兴了,太激动了,顺便在日记中多说上两句吧。   王管子老师原籍是新安县原仓头乡河窑村大河口仝家坡的,由于小浪底水库移民搬迁,搬到了原阳。算起来大概有晚近二十年没见面了吧。照片如见人,有种说不出的亲切的感觉。 我是听着王管子老师说的书长大的。记得我们孩提时代,还没有上学吧,那时候不知谁喊一声,来了说书的。我们一群娃们不敢听一声啊,就一边起哄:“来说书啦,来说书啦!”一边撵着说书的,跟在后边看,说书的在村子中间停下来,我们就围住他们,好奇地摸摸他们的弦子,敲敲他们的鼓。直到他们找着了队长,定下来黑地说书,我们才高高兴兴地散去,眼巴巴地等天黑,好听说书啊。 天黑了,大家早早地围在书桌前,围着一盏昏黄(在当时已经算最亮了)的马灯,鼓板大作,弦乐齐鸣,说书就开始了。小时候记得听过老杨先儿(杨得满,王管子的老师)的书,听过郭先儿的书,听过黄河北过来的说书人说的书,听过……反正多得记不清了,也叫不出什么名称了,但听过最多的,最熟悉的莫过王管子的书啦。为啥能记住王管子呢,这个名老少皆知呀。有人在书场毛捣:“听王管子说的书一股子王管子气。”被王管子听见啦,也不恼,反问:“王管子气是啥气?你闻过没有?”有一个小娃们接道:“一股子出离拐弯儿气。”众人大笑,王管子也跟着笑。这种玩笑开得很亲切,拉近了说书人与听书人之间的距离,气氛很融洽。如果认为这是对他的一种侮辱,就错了,相反的,他的名声却越传越远,人气越来越旺。 王管子善于说苦书,那天后晌,他说的是《拉荆芭》,说到苦处,声泪俱下,不住地用手绢擦泪,下边听众哭声一片,有几个老婆竟嚎啕大哭,书说不下去了,只得停下来,稳定一下情绪。王管子从书情里跳出来,笑着说:“看你们没出息那样,又没说着你们。”大家都又笑了,就是呀,这不是看闲书掉泪,替古人担忧吗。就这样,一场书下来,哭哭笑笑。要不会说“唱戏的是疯子,听书的是傻子”呢。 王管子说书特别形象逼真。记得我都上小学二年级吧,那晚上他说的是《南京风云》,说到黑大个杀赵玉莲的情景,一手拿钢板做刀状,一手摸鼓做人头状,缩头咬牙,嘴里恶狠狠地一声“嘶啦”,提着血淋淋的头飞出去了。我们都把他虚拟的动作当成真的了,听得心惊肉跳,看得浑身起鸡皮疙瘩。听罢书,我一个人得走一段夜路,吓得不敢回家了,脑子们老回旋着黑大个杀人的情景,怕黑大个冷不丁蹦出来,在半路哭了起来,一直等到哥哥来接。 王管子的身材特别魁梧,立到书场特别威风,腔特别浑厚,啜门特别亮,说书特别的镇场。有时候他在书场取笑说,大人们把小孩子的耳朵捂住,吓着孩子我不可管啊。你别说,有的孩子在下边乱窜,他吼一声,孩子们都不敢动了,乖乖地听书。 后来,我毕业了,也学了说书,吃了这门衣饭。我从王管子老师的听众变成了他的同行,有机会和他搭班,给他伴奏,给他合唱大书,更加深了对他的了解。他虽然不识字,但说出来的书词极讲究,每个词儿都要追根求底,问个明白。为人极其谦虚随和,平易近人。而他的名声也越传越远,威望也越来越高。 后来,说书不景气了,我不以说书为业了,我们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少了。 再后来,小浪底水库移民搬迁,我匆匆地搬到了孟州,王管子老师呢,也匆匆地 搬到了原阳。河洛大鼓的艺人们你东我西,再难聚到一块了。我们离开了老家,离开了养育河洛大鼓的沃土,就好象鱼离开了水,虎离开了山,没有了用武之地。我们走得离河洛大鼓越来越远,只有怀念,别无选择。 偶然从王管子老师的徒弟郭汉那里得到了他的电话号码,终于能通上了电话,但苦于事情羁绊,不能亲自拜访,就只好委托 朋友薜涛带劳了。 见照片如见人,王老师虽然威风不减当年,精神抖擞。但满头白发无情地告诉我,王老师老了!想到他老了,我心头又是一沉, 心里隐隐作痛。不是心疼他的苍老,而是心疼河洛大鼓艺术!这个孤单无助的老艺人,同孤单无助的河洛大鼓艺术一样,还能走过几多久?生命无法拘留,但艺术也无法拘留吗?是无法拘留,还是不想挽留,还是我们的挽留力度不够?靠政府蜻蜓点水,走马观花的挽留方式,河洛大鼓能留得住吗? 喜欢() 严正声明:本站文章可以分享,但未经允许,严禁转载,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 
看完了,点评一下呗!
还没有评论,快来抢沙发吧!
|
王管子的河洛大鼓
| 来源:本站原创 作者:吕武成 日期:2014年12月26日 点击量:次 | |
上一篇:戏说张天倍
下一篇:冬日里访河洛大鼓艺人王管子
|



 ;
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