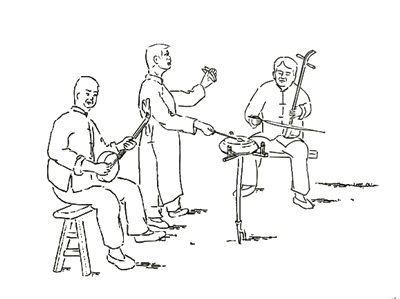|
怀念艺人王河清 吕武成 前天与济源同行伙计王小伟视频聊天,意外得知,我的从艺老师,新安县著名的河洛大鼓第四代艺人王河清因患食道癌医治无效,已于一个月前病逝,享年七十有九。惊愕唏嘘之余,不禁捶胸顿足,扼腕叹息! 王河清老师人品高,口碑好,是公认的“老好人”,不好事儿,不惹事儿,不得罪人,和谁都能说着话,合得来。难怪大家无不感叹:可惜这个人啦! 最早认识王河清始于1981年夏天在我们村说书。由于他长得高高大大的,我们村人都称他“大老王”。虽然是盲者,就是我们所说的“睁眼瞎”,但外观看不出来是失目之人,眼珠骨碌碌来回转,看似炯炯有神。如果不是他站起来摸着桌角往前面挪,用两手在桌子上摸鼓槌、钢板的位置,令人难以置信他是一个瞎子。他往书场一站,显得风度翩翩,抓起钢板摇了几下,掂起鼓槌敲几下鼓点,很是潇洒、自然。他的嗓音浑厚、纯净,富有磁性,听起来委婉、厚重而悦耳。 后来我学了说书,由王河清老师的书迷、崇拜者变成了同行。由于王新章、郭汉老师的牵连,我们在一块搭班、合作,他成了我的从艺老师。使我对王河清又有了更多的熟识和更深层的了解。 在新安县河洛大鼓界,尤其是失目的盲艺人中,王河清几乎是唯一的“文化人”“识字人”。他和王老师、郭汉的先天性失明不同,是“半路瞎”的。他上过高中,文化程度搁那个年代并不算低。毕业后当过几年大队会计,没有两下子能干得了吗?原本已经结婚生子,有了幸福的家庭,美满的日子过得滋滋润润的,谁不羡慕?然而厄运却悄无声息地袭来,二十八岁那一年眼上出了毛病,医学上叫“眼底出血”,后发展成重度“玻璃体混浊”,经偃师著名眼科医院多方面治疗无效,最终导致失明,成了“睁眼瞎”。 常言说,夫妻本是同林鸟,大难来时各自飞。夫妻之间,很多能做到“同甘”,却做不到“共苦”。不离不弃都是美丽的爱情传说,现实中凤毛麟角。王河清的失目,不但自己痛苦、绝望,家庭也陷入了黑暗的困境,看不到光明和希望。妻子几经犹豫、磕绊,最终选择离开,撇下三岁的儿子,狠狠心,跳起腿走了。眼底出血,使身体受到了伤害;家庭的变故,又使心底在滴血。屋漏偏遭连阴雨,行船又遇顶头风。雪上加霜,一连串的打击,一度让他萎靡不振,苦恼万分。以至后来每提到那段历史时,王河清都不愿多说,不想揭开那个沉重的伤疤。 小家散了,大家之中,亲情之间却温暖常在。他的父母,两个兄弟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和陪伴。眼看不见,闷在家中,不是个事儿,得找一个出路啊。失目人干啥都困难,于是他们就想到了说书。经过多方打听,周折,最终投正村东沟村的著名河洛大鼓第三代艺人王振松学艺。
王河清是我的半个老师。我学河洛大鼓时的唱腔、调门儿很大程度上受到他的影响。我学的几部大书《彩楼记》《刘镛下南京》《破镜记》《呼延庆打擂》都是在他的基础上引为我用的。 我们有很深的交情,很能说着话,合得来。从学徒到出师的十几年里,断断续续地搭班合作过。他为人谦逊随和,没有架子。学徒时,我尊称他“王老师”,他却反过来称为我“吕先儿”。难怪被俺老师王新章取笑:“你们这是乱套啦。”
后来,说书不行了,我移民搬迁到黄河北孟州,很难见面,更别提在一块合作演出了。唯一的一次是在2013年6月,俺老师王新章组织的见面会上,我们相见,欣喜若狂。当时他已过古稀,刚一见面,我有点不敢认了,岁月在他脸上刻下了深深的皱纹,记载了生活的艰辛。如果没有沧桑的白发,脱落的牙齿,当年的潇洒依稀可辩。这些年,说书几乎没有生意,在家里喂了两头牛,整日的铡草、垫圈、添草、添料。当年叱咤书坛,呼风唤雨的名家,现在除偶尔有一场演出外,大多的时间都是与牛为伴,闲时总不会“对牛弹琴”吧? 那一次,我们彼此叙旧,为河洛大鼓的前途和命运,我们谈了很多。临分别时,王河清老师紧紧攥着我的手:“武成,下一次咱们也不知还能不能再见面……” 我心里一沉,一阵悲怆涌上心头。是啊,当年的毛头小伙子,如今早已年过半百,成了“老头坯儿”。王河清也早已“哥亦不再是当年的哥”,渐入风烛残年了。河洛大鼓行有很多老艺人在我们的悲伤中离去,说不定啥时候就会轮到自己了。是啊,我们见面的次数已经进入倒数状态。当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时,立即拍着胸脯表态:以后保证每年都回新安看望你,保证每隔一段时间电话联系一次,等等。 情绪激动时信誓旦旦的承诺,回家来终因事务的繁杂而食言,种种的羁绊而搁置。以至如今,我们再没见过面。期间也通过几次电话,互问安好。 虽然说书不养人,但一直没有忘却或抛弃河洛大鼓。二十余年来,作博客,办网站,整理资料,出书……一切都在为河洛大鼓的挽留、传承而努力。伴随着河洛大鼓的渐行渐远,其情结愈加浓厚。河洛大鼓的往事点点滴滴,历历在目,便在闲暇之时,将自己的行艺经历,接触到的河洛大鼓艺人,以及有关河洛大鼓的风情民俗记录了下来,分章分节在河洛大鼓网、河南曲艺网和河洛大鼓公众号连载,得到了很好的反响。其中有几章浓墨重彩地写到了王河清老师。 去年夏天,我在外地安徽上班,打电话问候王河清老师。他在电话里依旧亲热、惊喜得不得了,依旧很爽朗地笑着。他说,除了耳朵聋以外,身体好得很,没一点毛病,让我尽管放心。我说,我正在写一本书,写一本河洛大鼓的书,里边净是些咱说书人身边的事儿。其中有些情节就写到了你。他笑着说,吕蒙正的后代没笨人,我早说吕先儿是个才子,能写会道,中,等写好了,啥时候念给我听听。我说,你等着,等我书写成了,回新安县,把有关你的情节亲自读给你听。 …… 做梦也想不到,这次的通话竟成永别!我不想接受这个现实,去年还好端端的王河清老师,怎么说没就没了呢?我好后悔和自责,成天总以繁忙为理由和借口,没能去看他最后一次,甚至在他去世一个多月才得知噩耗,酿成终身遗憾!他最终也没听到我给他念有关河洛大鼓的书,有关他的那些事儿! 这几日不能自已,夜不能寐,脑子里满是和王河清老师相处的点点滴滴,其音容笑貌不断浮现眼前。缅怀之情无以释放,驱使我写下了上面的这些文字,权作望空遥祭。如果王河清老师在天有灵,能感应到我的信息,则心愿足矣。 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