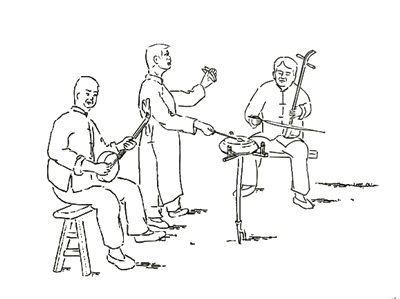|
我所经历的河洛大鼓系列之廿六
怪不得刘大江说书知名度不高,方圆左近知之者甚少,默默无闻。都吃亏他摊得多,嚼不烂,啥事儿都想干。这山看见那山高,那山看见这山好。干东行(hàng)想起西行,贩骡马想起猪羊,七十二行没有他不想去尝试的。他太不以说书为专业了,想起来了,高兴了,背起弦子拿着鼓,找伙计去说书。一有其它的事儿,就把说书撂一边儿去了。这不,夏天收罢麦,该出门说书了,刘大江却因家中事多羁绊,出不去门了。 八几年河南农村大部分地区盛行种植经济作物——烟叶,比起种粮来,收入还是相当可观的。挣钱多,但麻烦事儿多,付出的劳动也多。不说整地、栽培、施肥、打药、打叉、分批收割等一系列繁琐的管理程序,还得专门建造烟炕,后期炕烟,分批次挑拣,排队卖烟等,都是相当吃功夫和花费时间的。 刘大江是不会放过这个种地挣钱好机会的,一下子种了五亩烟。麦罢和伏里天正是炕烟、卖烟的黄金季节,也是忙得连放屁都得跑着放的时候,哪顾得上出门说书?说书挣个仨核桃俩枣儿的,哪能和卖烟的收入比?刘大江小算盘打得山响,他不会为了贪图说书这个“芝麻”,而丢掉“卖烟”那个西瓜的。二选其一,忍疼割爱,这可怜的说书就被他狠心地暂时抛弃了。 我忿忿不平:“刘先儿,你弄这叫啥事儿?该出去说书,屎憋屁股门了,你突然变卦,不出去了,在家炕烟哩,叫我咋办?事到临头,去哪里找搭档?这不是毛捣人嘛。” 刘大江嘿嘿地笑着:“吕先儿,要不你给我照护着炕烟吧,一边干活,一边说书,我给你掏工钱。” “爬一边儿去,想哩倒美,你当地主,我堂堂的说书先生给你当长工?” “那咋弄?要不你再找个人出去?” “吃哩灯草,说得轻巧,到这时候了,是说家儿(说书的)都出去了,你叫我去找哪个老禇?” “我说这个人保险没出去。”刘大江开始给我支招,“你去找后骆岭的王矿子吧,叫他给你拉着弦,不就开开戏啦?” 我几乎跳起来:“你可拉倒吧,王矿子光会拉两下弦儿,一个字儿都不会说,指望我一个人领大书会中?” “咋不中?以前跟你老师厮跟着,缩进老母鸡的翅膀骨下,连一段儿大书都不敢说。咱俩一块出去,不是慢慢磨炼着会说大书了?虽然你现在能说大书,但和我一起有依赖性,缺乏独立自主,独挑大梁的能力。常言说,有山靠山,没山独担。现在我不跟你在一块了,才是真正锻炼拉正套儿,领正书的机会。只有经历了这个艰苦的锻炼和实习的过程,才算真正学艺到家了。趁我不在,好好把握这个机会,偷着乐吧。” 经刘大江这一番鼓动和撺掇,我还真有点动心了。说得没错,眼下虽然会说大书,但充其量是给人家当个副手、配角,领不住正套儿,坐不上第一把交椅。如果刘大江不在,岂不是“山中无老虎,猴子称大王”了?当上一把手,凡事自己说了算,想想都振奋。但心里还是没底儿,有点胆怯:“刘先儿,你这是憨狗戳老歹,中不中?我都没领过班儿,没有好说家儿,拉家儿又不咋的,出去会弄成事儿?” 刘大江笑道:“不用嫌拉家儿瞎,初学领大书,好拉家人家还不一定想侍候你哩。去吧,只当出去闯书[①]哩。只要不怕吃苦、受累、多操心,肯定中。你没听说,不受苦中苦,难熬人上人,苦尽才能甘来。去吧,听我的没错。” “那你说,我领着矿子出去试试?” 刘大江继续打气:“不用试,一试都中。有道是,闯一闯,长一长,不闯不长,老鼠的尾巴,发不粗,长(zhāng)不长(cháng)。大胆出去?闯啦,撑死胆大的,饿死胆小的。说书也一样,一分胆量一分成功。老是畏畏缩缩,啥球事也弄不成。” 当我跑二十多里山路,到后山骆岭的小南沟把王矿子接到家中,向家人说明打算单独领班出去说书时,首先遭到了二哥强烈地反对和劈头盖脸地训斥:“能轻点儿吧!自己那两下,有多大本儿不清楚?还单独出去说书哩,不说挣钱混饭啦,恐怕连口凉水也混不到嘴里!不用丢人现眼啦,赶紧把人家送回去!要么还去坡顶上找你老师儿一块出去,要不就安安生生地爬在家里种地,没事儿跟我去竹园进窑。” 唉,俺弟兄三个,大哥宽厚,从来对人和气,二哥能说会道,比较能干和强势,又比我大一轮儿(十二岁),作为小弟,挨他训是家常便饭。没办法,人家是哥哩,对不对都得听,话头儿轻重,都得伸伸脖子咽下,不能反驳和顶撞。再说二哥话糙理不糙,也是担心我出去混个失魂落魄,狼狈不堪,惹人见笑啊。突然间一个人出去闯天下,大家无法接受这个现实,为我担心,替我着想,心情岂能不理解? 对于二哥的一番指责,我“阳奉阴违”,表面上唯唯诺诺,做一副惟命是从的受训状。等他去窑一走,迅速收拾行李,立马启程。老母亲尽管有千般牵挂,万般唠叨,却挽留不住儿的一片野心,挡不住儿出门的脚步。只好开笼放雀,依依不舍地打发我们出门,颇有“顿开玉锁飞蛟龙”之悲壮。 牵着王矿子,逶迤在石井北山的山道上,感受到肩上包袱沉甸甸的份量。这是我自脱离王老师以来,摆脱刘大江之后,凭着一腔激情,一股冲动,无视家人劝阻,一意孤行,孤注一掷的第一次独立行动。都知道,王矿子仅能给我拉个弦儿,做个伴儿,充个人数,仅此而已。其它地方甭想指望他帮上任何忙,还陡增了照顾他的负担。给盲者领路,侍候他的生活起居;往哪个方向走,黑了落脚在哪里;到哪个村,找哪个队长,咋联系生意;书场说啥书,是文还是武,是悲还是喜;吃罢了这顿饭,下顿在哪里?……这一切一切的麻烦事儿,统统地压在一个人的肩上,没有人会替你分忧解难。用我们老家的话说,就是要连稀带稠一齐吃,连打带搧一起来。热劲儿冷下来,面对的是严酷的,无法逃避的现实。事到如今,已经是骑虎难下,覆水难收,箭在弦上,不得不发,只好硬着头皮,仰摆脚儿[②]尿尿,流哪是哪吧。 山路迢迢,前途渺渺。想再多也无用,也不会有人替你分担。我明白,关键时期,更要保持沉着、冷静。不能先自己乱了阵脚,不能有半点儿的气馁和灰心,更不可打退堂鼓,未曾交锋,先败下阵来,做了逃兵,落下笑柄。正应了那两句戏词儿:“明知征途有艰险,越是艰险越向前。”往前走吧,别无选择! 临近傍晚,我们在下石井北边的晃庄写住了第一场书。那晚上书说得还算顺利,虽不算叫好,但至少没有出现大的纰漏,总体还可以。就是一气唱两三个小时下来,不记得擦了多少次汗,到最后已经没汗可擦了。两眼发朦,头发胀,喉咙发干,嗓子冒烟,好像柴油机要烧缸一样。腹内之气直往上攻,聚在胸口处,堵在气管口出不来,闹得连夜餐也吃不下去。刹罢书往椅子上一蹾,半天不想起来。头一次一个人一口气唱一场书,那种苦,那种累,无以言状。 有的说,你这说书的说得也太张精[③]了吧?你们说书的,既不肩挑手提,也不背背扛扛,不就是嘴皮子一张一合,上下动弹两下嘛,会累成那样? 说这话的都是外行。但凡说书唱戏,卖喉咙,恁嗓子吃饭的都知道,唱的声音看似从嘴里出来的,实际发声是需要用气的。气从哪里来?气从丹田出,绕五脏,经六腑,带动三百六十五个关节,最后经过喉咙而发音的。这就是卖力、投入的艺人为啥唱时浑身乱动弹的道理。说书唱戏看似嘴皮功,实则是局外人感受不到的重体力活儿;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并举,既操心劳神,又费气费力的职业。我说这话你不信,打听一下身边熟悉的说书艺人,哪一个没经历过这种艰苦的磨练,没有这种刻骨的体验?人们都说“钱难挣,屎难吃”,我还得加上一句“书难说”啊。 第二场书在石井的刘洼村。一个老头当“牌官儿”,出面收粮食,每户收一碗玉米,卖了钱后说一场书有余,原打算说两场的,结果次日晚上有电影,只好作罢。我们就沾了个光,再换地方。 第三日调整了一下方向,下到青河川一直向西,过胡庄至红孩寺时,青河一分为二,左为龙潭沟,右为山沃街。走哪边呢?山沃是大村,只所以叫“山沃街”,肯定在石井后山来说,比较热闹繁华。听说山沃的戏不好唱,书不好说,恐怕到那里打不出,还是不去吧。龙潭沟听说有好多景致,如龙潭、刀掉石、皇姑庵啥的,可有看头啦。那就上龙潭沟吧,就是说不成书,去看看风景也不亏呀。于是左转,朝龙潭沟摸去。 事实证明,我这个算盘打错了。那时候的龙潭沟还没有开发,不是旅游景区,还相当贫穷落后。我们到了龙潭沟最大的一个村——骆村,找到了队长,好话说了八千,把郭汉老师教给我的生意经几乎全部用上了,无果。人家队长说,队里实在没钱,说不成书,不过还算念我们出门人难,混了一顿饭,打发离庙。 越往后沟越来越深,山越来越高,人烟越来越稀少。领着矿子走山路太不方便,不敢再深入了,只好悻悻地原路折回。 重返红孩寺的三叉路口,在路边的代销店稍作休息,盘算下一步咋走。红孩寺,叫法不一,也有叫“红崖寺”的。众说纷纭:前者源于《西游记》中的红孩儿除妖有功,建寺纪念;后者源于此山有一片山崖是红的,叫红崖山,山上有寺,故曰“红崖寺”。从当地人的口中,叫“红孩儿寺”的居多。有关红孩寺有诸多美丽的神话传说,让人充满神往、憧憬。限于篇幅,不敢跑题,只好忍疼割爱了。 似乎有个小庙一般的房子,在半山崖中,掩映在绿郁葱茏之间。有心爬上去看看,说书还没有着落,哪还有如此闲情雅致?还是算了吧。 听不到寺院钟声,却传来了朗朗的读书声。原来两河正交叉口,代销店背后,坐落着一座规模像模像样的学校——红孩寺中学。据说是在原红孩寺院的基础上改造成学校的,山上看到的那座房子只是红孩寺的一个小建筑而已。 正一筹莫展之际,学校的一位老师来代销店买东西,看见了我们的弦子和鼓,有点惊奇似的:“咦,说书的?”以我的经验,学校是教书育人的地方,很少说过书,大概怕影响孩子学习吧,所以我心不在焉地“嗯”了一声。谁知那个老师竟然说道:“走吧,到学校院里说一段试试,中啦,就说两场。”我一听,有门儿!立即打起了精神,忙不迭地答应,赶紧拉住矿子,背起弦子,那位老师抢过鼓包,替我们拿着,屁颠屁颠地进了学校。 事后才知道,这位老师叫李克民,石井南山人。在学校是教导主任,学生老师们都喊他李主任,是除了校长之外的第二把手,掌实权的,说书不说书,都是他一句话的事儿。李主任,我领班说书遇到的第一个贵人,好心人,是他在干涸的旱季送来了甘露,在瞌睡时递过来个枕头,在孤独无助时,及时伸手扶了一把,我一辈子都记着了他的名字。 机会来了,有生意了,我却忐忑不安,心里含糊,没一点底气。喉咙长时间不唱的话,称为“荒喉咙”,老师们不止一次地说过,刚开始的荒喉咙唱着不顺,不稳定,不耐用,容易嘶哑。嘶哑后硬唱过来的喉咙才算正常。初次领大书,荒喉咙满负荷地使用,加之缺乏经验和用腔技巧,死唱,硬唱,两天下来,喉咙已经哑了,说话都有点费力,嗓音明显变坏。这样糟糕的嗓子试书能成吗?有几分胜算?会通过李老师的“考试”吗,能及格吗?说实话,真没有多大把握。但好不容易有个机会,岂能放过?只好硬着头皮上吧,是福不是祸,是祸躲不过。管他哩,碰碰运气吧。 我说了一段《罗成算卦》,尽量避开腔不好,嗓子哑的劣势。高音顶不上去,就尽量在低音部盘旋。虽然不高亢明亮,却也有些沧桑厚重感。唱着不得劲儿,就尽量“三分唱腔,七分白口”,少唱多说。一段书下来,再三拱手向李老师他们表示歉意:嗓子哑了,发挥得不好,不能让老师们满意,真是对不住大家了。 谁知大家竟然拍手叫好。李老师说:“哑了好,说书就是哑哑的腔听着才入耳呢。中,说得好!不用走了,今晚上就在学校说(书)。”嘿,考试顺利过关。 晚上开的书是《彩楼记》,前半本《吕蒙正讨饭》,后半本《吕蒙正中状元》。听书的大多数都是老师和留校住宿的学生,附近胡庄村闻讯也来了一部人。结束时,李老师问,这部书得说几天能说完?我回答,这是一部小书,三天就说完了。李老师说,好,我们就说三天,听个有头有尾。嘿,续上茬儿啦,明天、后天都安排住了,我终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。 第二天,李老师说,夜里说书,不在学校住,走读的同学们听不成。为了照顾所有学生都能听到说书,建议搁白天演出。作为说书的,出门人,当然是客随主便,人家咋说,咱咋执行啦。 不愧是学校,和农村说书就是不一样。谁说“学生,学生,赛过猴精”?学生在家中调皮捣蛋,不服家长管教,但到了学校,见了老师,就好像老鼠见了猫一样,规规矩矩,老老实实。这不,在李老师的组织下,学生们按班级排队,坐得一行一行的,横平竖直,井然有序。既不交头接耳,也不大声喧哗;既不像农村那样,在书场上窜下跳,跑来跑去,也不像在农村那样,又吵又闹,扰乱书场秩序。 我在上面静静地说(书),学生们在下边像听老师讲课一般认真地听,不服气人家学校的校风正、纪律严、规矩好不行啊。说书休息的空隙,李老师还要插播一段话:“同学们哪,叫你们来听书不是白听的。听听人家吕蒙正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是怎样刻苦学习的。白天要饭,夜间在寒窑还要用香头照字读书。相比之下,我们今天的学习环境好多了。同学们哪,我们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,像吕蒙正那样勤奋学习,将来成为国家横梁之才啊。” 呵呵,俺老师没想到,我也没想到,我们经常唱这个吕蒙正只是为了娱人,做茶余饭后的消遣,却被李老师提升到了“育人”的高度,成了教育学生好好学习的良好素材。不得不服气,教师就是教师,文化人就是文化人,看问题,理解问题的深度和高度是我们说书人不能及的。 学生后面聚集了一片当地的村民,有胡庄的,有百姓沟的,有山沃村的。刹书后,李老师朝后面招手:“明朝,占国,过来!”应声便从后面走出两个年轻小伙。李老师向我介绍道:“这俩都是我教出来的学生,山沃村的。”又转向两个小伙,“你们听人家这书说得啥样儿?”俩小伙忙不迭地点头:“说得中,老美啦。”李老师命令道:“说得中,你俩就回去找找队长,把说书的领到你们村说几天,这任务就交给你们了,能不能完成?”老师发话,谁敢不听?俩小伙儿拍拍胸脯:“老师放心,保证完成任务。” 这两个小伙在红孩寺学校校舍内干点杂活,一个叫张明朝,山沃街东头的,一个叫陈占国,是西头的。就这样,张明朝、陈占国在李老师的介绍下,成了我山沃说书的牵线人。此后山沃说书的一二十天时间,我们成了铁哥们,好朋友,每天都差不多形影不离地猫在一起,替我山沃说书推波助澜,帮了不少大忙啊。说书闯山沃成功的背后,至少有三分之一应该归功于他俩。 由于李老师这个“媒人”给力,威望大,能号令学生;两个小伙儿的线扯得长,牵得紧,活动能力强,山沃大队所有的生产队长都能搭上腔,说上话,吃得开,叫得响。所以山沃说书,我几乎没有操一点多余心,跑一点冤枉路,一切水到渠成。红孩寺说书一结束,就顺理成章地跟着我的两个铁哥们儿张明朝、陈占国浩浩荡荡地进驻山沃。 “山沃”是书面上的写法,也作“山窝”,当地人可能音念转了吧,都叫的是“沙窝”,又被戏谑称“杀我”。千万别小看这个藏匿在石井后山密林中的小村落,具有悠久的历史和厚重的文化底蕴。明清时期曾是石井直达渑池县的必经之路,也是沟通洛阳至山西垣曲的交通要道,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不言而喻。村中保留的清代驿站——骡马店,还有斑斑驳驳的青石板路,一切都见证着这里曾经的车水马龙,热闹繁华。山沃虽山,却经过大世面,见识过形形色色;深藏不露,却知名度极高。 能在这样一个大村说书站得住脚,打开局面,是我始料不及和引以为豪的,也有了日后向王老师、刘大江吹嘘、炫耀的资本。 经历了晃庄、刘洼、红孩寺五天说书的磨练,由荒喉咙唱到嘶哑,再由嘶哑硬唱了过来,更变得稳定和磁实了,也积累了一定的用腔技巧。等在山沃开始第一场打门面书时,嗓子已经调整到良好状态,发挥了更好的作用,为唱响第一场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,结果一切如愿以偿。 《彩楼记》和《双锁柜》都是小本头书,每部书只能唱三天。在山沃东街说了六天,两部书都说完了。到西街时,一位老头——一个老书筋[④]问我:“小伙儿,会说大本头《刘镛下南京》不会?” 《刘镛下南京》是俺老师王新章和王河清老师的拿手书,我听了N遍,情节早已了然于胸。可仅是听过而已,从没有机会实践过,这能算会吗?可为了那一点自尊心和好强心,明明没有说过(这书),却还要打肿脸,弃胖子,硬着头皮地满口答应会说。几个老头就说:“那就开大本头《刘镛下南京》吧,说个十天半月,听着有劲儿。这些小翻针线筐儿书还没说哩,完啦,听着不过瘾。” 大话撂出来了,收不回去啦,到西街的两个队只好开了《下南京》。好在情节比较熟,又多是丁咚辙,韵脚宽,好抓词儿,竟也顺利地拿了下来。尽管那几个老书筋很懂行,很挑剔,却也没有挑出什么毛病。几场书下来,获得了他们的赞许和认可。更出人意料的是,有几个精彩之处竟然特别叫好,一板书连鼓了三次掌,书场气氛极其热烈。甚至有人评价,这是有史以来,见过一趟说书的,都没这个说书的说得好。 有人笑了,你这说书的,就捏住鼻子瞎喷吧,就你那两下,真敢说得出口!见过老王卖瓜,自卖自夸,没见过你这说书的嘴,自吹自擂!你还别说,我自己都有点不相信这是真的,但却是实实在在的事实,没有一点水分,不信你跑山沃去打听一下。 事隔多年以后,现在回想起来,那时候说的书啥都不是,全仗着年轻,敢想敢干,有冲劲儿,有迸劲儿,会蛮干,会胡来。不知道天有多高,地有多厚,无知者无畏,赤肚子[⑤]撵狼,憨胆大,初生牛犊不怕虎。至于说为啥能叫好,获得大家的肯定和认可,也不过是瞎猫碰着死老鼠罢了。 山沃说书时间长了,人也熟了,风言风语却多了起来。白天没事儿走在街上,总是一些年轻媳妇和姑娘们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,一边衲底子,捻麻绳儿,做针线活儿,一边儿却是“东家长,西家短,你的鼻子他的眼”地品头论足,“黑嗒嗒,黄嗒嗒,热屁股墩到冷地下”,有一搭没一搭地拉着闲话。看到我过去,立即止住了话头,斜着眼看人,神情怪怪的。原来不是这样啊,见面还要打个招呼,问吃饭没有,等等。这是怎么了?好像有话在刻意回避我。等我过去,她们或暗地指指戳戳,或悄声说点什么,或捂着嘴偷笑,弄得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,不知道她们葫芦里到底卖的啥药。 这天张明朝找到我,开始盘问:“伙计,你不够朋友,有人给你写情书了,还瞒着俺们。” 我一头雾水:“这都哪跟哪的事儿?净瞎说,谁给我写情书了?” 张明朝笑道:“装哩怪像。这两天都传明了,都在议论这事儿,难道你不知道?” 我急了,连说带赌咒,伸着指头比划着:“我要是知道,我就是这么高儿的小鳖儿籽儿。快说说,到底是咋回事儿?” “回去看看你的那个工账本本儿,在中间页面的背后写着哩,别人都看见了,闹得满城风雨,你还蒙在鼓里,真服了你啦。” “还真有这事儿,我咋不知道呢?叫我赶紧回去看看。” “没风能起浪?好吧,你回去找出来,赶紧撕掉,影响太不好了。你没有媳妇,她没有婆家,男婚女嫁,正常谈恋爱,这都没有啥,俺们还能帮忙促成。关键是人家有婆家了,这事儿闹大了不好收场啊。” 张明朝的提醒和担心不无道理:山沃说书,人家是经纪人,亲自引进过来的,万一出点啥事儿,说书人把山沃的闺女拐跑了,人家脱不了干系啊。 我一边儿唯唯诺诺地答应,一边心急火燎地回到住处,翻看那惹祸的,倒霉的工账本。 这是我刚出学门,给生产队当记工员留下的工账本。前面提过,给郭汉老师抄写《花草集》时,也工工整整地复制了这一份儿,成了我说书必备的工具书,随身携带,得空儿又读又背。我这人比较“郎当[⑥]”,随意,东西走到哪,丢到哪,不知道金贵。该换地方了,才手忙脚乱地收拾,又往往丢三落四的。这不,由于没看好自己的东西,被人做了手脚也不知道。 果然,在《花草集》正中间内容页的背面找到了所谓的“情书”,16开纸歪歪斜斜地写了大半张,结尾竟然堂而皇之地落上了自己的名字——春玲。说是情书,写得一点儿也不浪漫、委婉和含蓄,话说得很直白,可见写字的人文化水平高不到哪去。啥内容现在已经记不清了,只记得最后两句的大概意思是:我很喜欢你(那个年代,农村人没有情调,情呀,爱呀啥的说不出口),我很想跟你走,但又不敢……云云。 这个春玲,不但认识,而且还见过几次面,说过几回话,比较熟识。对她的印象确实很好。第一次见到她,正从山上背了一捆柴禾下来。一二十岁的姑娘家,在崎岖陡峭的山路上,背着百十斤重的东西,竟然行走如飞,非常麻利。不得不佩服山里的姑娘勤劳、能干,将来肯定是持家的好手。第二次见面,她和几个姑娘有说有笑地飞针走线,佩服农家的姑娘针线活真棒,心中已有几分好感。第三次见面,我们聊了些闲话,发现很能说得来,尤其她那一双水汪汪的大眼,会说话似的,令人动心,勾人魂魄。此后我会有意无意地找她搭讪,无话找话地制造话题。她呢,一个人不好意思,总会攀上一两个伴儿,有事儿没事儿地找到我们的住处,嘻嘻哈哈,半真半假地摸摸弦子,敲两下鼓,装模作样地翻几下书。她们的到来,当然是来者不拒,大咧咧地让她们随便摸,随便翻,随便看。谁知道,就在这翻翻、看看、摸摸之中,竟然神不知,鬼不觉,不知什么时候留下了情书。你知他知人人知,唯有我不知,唉,太粗心大意了。 我赶紧忍痛割爱,小心翼翼把正面载着《花草集》内容的情书撕下,放在贴胸内衣的口袋里,算是藏匿了证据吧。心里小鹿般乱撞,乱跳,久久不能平静,怀揣“情书”,想了许多…… 从当面交谈和侧面打听,关于她,我知道得不少。和我一样,她早年丧父,母女们相依为命,大有同命相怜,惺惺相惜之感慨。她有婆家,是山沃后面杨家庄的,是娃娃亲,两姨结亲,是父母做主给订下的。两个人很少交往,更谈不上啥感情。她说过,不想从大山里走向更深、更高、更山的山窝窝。和许多山里姑娘一样,做梦都想飞出大山,扑向外面更精彩的世界,谁也摆脱不了这种很现实,很世俗的理想。这些,她在写给我的情书里很明显地表达了出来。 但现实真的很无奈,如好哥们儿明朝所言,宁拆十座庙,一坏一桩婚,破坏人家婚姻,损人利己是不道德的,会遭人谴责的。可放弃了,心里又一阵阵地隐忍作疼。 此后,因为处在风口浪尖之时,我们都要避嫌,彼此不敢再见面说话,背后有无数双眼睛在盯着我们。随着山沃说书就要结束的临近,心越来越失落。终于在临近结束的前一天,晚上刹书时,乘人们进进出出的混乱之时,她大着胆子,挤到了桌前,趁人不备,急急地塞给我一张纸条,转身而去。人走完了,我偷偷展开一看,六个字:今夜晚,村后见。 山里的夏夜,月色如银。当我心不在焉,急急地吃罢夜饭,匆匆地赶到村后赴约时,她已经等在月光里。我充满歉意地站着,一时不知说啥是好。几天来准备了千言万语,却憋烂在了肚子里倒不出来了。有很多话要说,有很多事要讲,可一时噙着冰棱倒不出水儿来。很恨自己不争气,平常书场内口若悬河,滔滔不绝的本事上哪去了。她也是,平常倒也伶牙俐齿,说起话来机关枪似的,怎么这时候也卡壳啦? 咱是男的,总得主动点吧?我抬头看天,无话找话:“月,亮,真,好!” “嗯。”她糯糯地说,“夜,真静。” 我沉默,她沉默,又是一阵沉默。 她先打破了寂静:“那,你看了吧?” 她嘣出来的这几个字触发了我的开关,打开了话匣子,把话题引出来了。首先,我严肃认真地批评了她的错误:“看你弄这叫啥事儿?写信上哪里找不来纸,偏偏要写在我书页的背面?写就写了吧,你倒是告诉我一声呀!这倒好,我还没看到,倒叫别人先看去了,传得沸沸扬扬,弄得咱这样被动。唉。” 她说:“信纸不是没有,不是写出来不好意思给你嘛。再说,一直没有机会,也没法跟你说嘛。我想着,你成天拿着那个本儿读呀,背呀,会发现不了?谁知道别人能看到,你却看不到!唉,我也想不到事儿会到这种地步。” 算啦,事儿出来了啦,多说无益。我又继续第二个话题,严正地声明了我的立场和态度:“你的事儿我知道,也一直对你有好感。可你已经订婚了,尽管对这门婚事不满意,但还没有退婚啊。如果我这时候插手,情不正,理不顺哪!更不能有私奔的想法,那样你对不起父母,我对不起朋友,弄得里外不是人啊。如果你有情,我有意,就和你娘商量好,跟对方退婚,好说好散。到那时,我找媒人光明正大地来个明媒正娶,风风光光。” 她叹了一口气:“十多年的亲事啦,又是亲上加亲,亲戚摞亲戚的,哪能说退就退?已经闹了几年了,还没结果。和和气气,好说好散的希望不大……” 我无言,她无语,又是一阵黯然的沉默。 “哽,哽——哽——”不知哪个傻吊公鸡,已经拍打着翅膀开始啼叫了,一声鸡鸣,划破了寂静的夜空。 “夜深了,该回去了。”她缓缓地说。 “嗯,你走吧。我回头等你的信儿……” 她又表情复杂地看了我一眼,然后慢慢离去。 我站在原地,目送着她。 她走了几步,回眸一望,见我没动,就又停了下来。四目相顾,再伫立良久。 又一声鸡叫,村内传来犬吠之声,一呼百应,此起彼伏。我担心被人发现,麻烦更大,一狠心,挥了挥手,转身头也不回地走了。 这一夜,无眠…… 写到这里,自己都为第一次毫无经验,生涩的约会和恋爱感到好笑。这是在约会,谈恋爱吗?咋感觉是在谈判哈。那个时代,那个年龄,现在回想起来,太老实,太迂阔,太不会办事儿。天地良心,说是约会,在那个寂静的夜里,美好的时刻,只是远远地站着,谈了几句说恋爱不像恋爱,不咸不淡的话。积累了几天的相思,备课了无数遍的情话,“甜言蜜语”,临到用时,说出来却变成了那样的口味。除了心灵的碰撞,眼神的交流,双方连手都没敢碰过。换做现在的青年人,可能吗? 自此一别,再无相见。我也没能等到她的信儿。可能她对我也失望了吧:只想说书的能说会道,聪明灵活。殊不知遇上个老实蛋儿,囟球货!哈哈。 [①] 闯书:说书行中,艺人俗语,把锻炼说大书、说新书,或生涩的书称为“闯书”。 [②] 仰摆脚儿:新安方言土语,也称“仰摆叉”,四面朝天躺在地下的意思。 [③] 张精:新安方言,夸大事实,虚张声势,有意做作。 [④] 书筋:这是区别于评书的“书筋”。河洛方言里把特别懂戏和懂说书的人称为“戏筋”和“书筋”。 [⑤] 赤肚子:新安土话,没穿衣服,赤条条的意思。 [⑥] 郞当:新安方言,不受约束,随便之意。 |